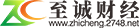辛德勇读《红楼梦》|我的“怡红院群芳夜宴图”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虽然没有直接言明主人公贾宝玉的生日是在哪一天(案我考证应该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别详拙稿《贾宝玉的生日是在哪一天?》,待刊),但却浓墨重彩地描摹过一次贾宝玉过生日的场景——在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和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艶理亲丧》这两回,几乎用了整整两回的篇幅,很详细地展现了宝玉的三场生日宴。
《红楼梦》剧照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为什么用这么重的笔墨来书写这次生日?这事儿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过从贾宝玉的年龄这一角度来看,到这一年的生日(十三岁生日),他就过满了十二周年,而“十二”是个“天之大数”——或许这是曹雪芹考虑的因素之一。
宝玉的这三场寿筵,是在贾母、王夫人以至贾珍、贾琏等人都因遵制为老太妃送葬而不在家中的情况下举办的。第一场,大致是在半上午的时候,按照“定制”安排的生日宴。不知是不是由于老太妃去世而“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这个缘故(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还是由于贾母和王夫人、贾珍、贾琏等都不在家的原因,包括薛姨妈、李纨、宝钗、黛玉等在内的一众人等(凤姐在养病,所以没有参加),只是“同到厅上去吃面”。第二场,时间是在半下午的时候,名义上是探春张罗凑份子,给同一天过生日的平儿办席,地点是在大观园内芍药栏中的红香圃三间小敞厅里。第三场,是在这一天的天黑以后,原本是宝玉身边的丫鬟们在怡红院里私下为他庆寿。
说这上午的第一场寿筵是按照“定制”正式安排的,是基于如下两点。第一,书中述及这个日子,就说“因为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闹热”,说明按照规矩这个生日是年年都要过的。第二,寿筵开始前大家才知道这一天也是平儿的生日,于是探春决定大家凑份子同时也给平儿庆寿(实际上是同时给贾宝玉、薛宝琴、邢岫烟和平儿一同过生日),“探春因说道:‘可巧今儿里头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揽了去,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众人都说是极”。当探春“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儿是平姑娘的华诞。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开了账和我那里领钱。’”(第六十二回)这“里头厨房”或称“内厨房”,指的是大观园里的“小厨房”;“外头”的“外厨房”,则应该是统管整个贾府的“大厨房”。柳家的说“外厨房都预备了”,自然是按照贾府常规给贾宝玉预备的庆生宴席,这也就该是半上午时吃的那顿寿面。
《红楼梦》剧照
相比之下,接下来的第二、三场寿筵就显得要随意很多。第三场筵席是由宝玉身边的丫鬟张罗起来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其随意性会有多强。第二场的情况,如上所述,既然出自“大家凑份子”,当然也不会是确定的章法。如平儿所云:“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因而一向都是“悄悄的过去”。
当前两场筵席结束之后,宝玉和袭人商议,晚上他要和自己房里的丫鬟们吃酒取乐。袭人告宝玉,她和晴雯、麝月、秋纹以及芳官、碧痕、小燕、四儿这八个丫鬟已经为晚宴凑下份子,“预备四十碟果子”。用袭人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第六十三回)。后来虽有李纨、宝钗、黛玉、探春、湘云、宝琴、香菱诸人加入,但她们都是宝玉特地请来的。宝玉既是寿星老,也是晚宴的主人,这一性质并没有改变。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回目的前半段“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指的就是这一天晚上举办的这第三场宴会。由于曹雪芹在书中对这场宴会的细节描摹得相当充分,激起读者对宴会场面的强烈兴趣。于是,就有好事者尝试复原当时的席次——这也就等于复原出一幅《怡红院群芳夜宴图》。在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中,我见到有三位前辈学者,相继做过这种尝试——他们分别是冯钟云、俞平伯和周绍良先生。
诸多学人之所以对复原这种《怡红院群芳夜宴图》有这么浓烈的兴趣,是因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书中既没
有清楚写明这场夜宴席次的安排,但实际上又通过色子(书中写作“骰子”)点儿的形式,暗暗地讲出了主要人物在宴席上的坐位(这些人已占与席者总数的四分之三)——庆寿当然要喝酒,喝酒就要行令,这次行令的方式是掷色子,占花名:色子点儿数到谁,谁就从签筒中掣出一只花名签儿,再按照签儿上的令来饮酒;然后由这次掣签者投掷下一次的色子,递次进行。
本来只要细心从事,做这样的复原工作并不困难,可是由于这三位学者依据的《红楼梦》文本都有问题,即色子的点数存在明显讹误,而他们彼此之间对如何订定这些文字讹误见解存在分歧;同时,如何理解书中其他相关的记述,这三位学者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这样就造成了三人各有一幅《怡红院群芳夜宴图》的局面。
冯钟云先生的文章,发表在1948年4月6日的北平《新生报》上(此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合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文章没有附图。这样的内容,若是单纯依赖文字描述,理解起来实在困难,所以在这里我就先用示意图的形式,将其结论表述如下(粗黄线条表示炕沿,又冯文明确表述说宴席上用的是拼起的两张“方桌”):
冯钟云的《怡红院群芳夜宴图》
看着这幅图来说话,下面的叙述就比较容易了。
首先,书中所记掷色子行酒令的程序,可以简括如下:
晴雯——六点——宝钗
宝钗——十六点——探春
探春——十九点——李纨(令云“下家掷骰”)
黛玉——十八点——湘云
湘云——九点——麝月
麝月——十点——香菱
香菱——六点——黛玉
黛玉——二十点——袭人
根据这样的点数,大致可以判断,冯钟云先生当时依据的《红楼梦》,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在1927年出版的铅字排印本,即红学界通称作“亚东本”的那个版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是社会上普遍通行的本子,所以俞平伯先生和周汝昌先生阅读的应该也是这个版本。
这个印本的底本,是程乙本,也就是程伟元和高鹗第二次整理印行的萃文书屋木活字本。谈到诸位学者所用《红楼梦》的版本,我们首先需要清楚了解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一项重要特征——即一般来说,其文字错讹是相当严重并且大大高于雕版印刷的。这也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普遍通行的原因之一。
数字在文本流传过程中本来就很容易出现舛误,了解活字印刷这一特点之后,我们就会更容易理解,这场群芳夜宴席上掷出的色子点儿点数出现差错,是十分正常的,不足为怪。
这种点数的数算方法,同打麻将分牌一样,也可以说所有这种棋牌类博弈色子点儿的算法都一样。因此,对打过麻将的人来说,是一清二楚的,即从掷色子的人本人开始向右手的下家数算,本人是一,右手第一人是二,第二人是三……,依此递增,最后那个数轮到谁,谁就掣签,席上人依签令饮酒。
由于存在文字讹误,按照上文简括的色子点数,是不可能排出这场夜宴的席次的。冯钟云先生的判断是:(1)湘云掷出的九点,应该是八点。(2)麝月掷出的十点,应该是四点。关于前者,冯钟云先生以为这“或是作者一时疏忽,错算了一点,实际上只数了八点”。后一处则属文本讹误,盖“十与四声相近,可能引起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讲述的色子点数,没有涉及秋纹、碧痕、小燕(程乙本作“春燕”)、四儿这四个角色,在我依据冯文绘制的这幅《怡红院群芳夜宴图》上,秋纹的席次,是冯钟云先生根据她的地位所推定。另外,冯氏谓小燕和四儿地位最卑而碧痕稍高,所以我在图中做了那样的安排,只是小燕和四儿孰高孰低,冯氏未做评判。
单纯看他的说法,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可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俞平伯先生在审辨色子点数的讹误时,推断的错谬之处与冯钟云先生相同,只是他以为湘云掷出的九点“疑为十之误”,麝月的十点“疑下脱一‘八’字”,即十点应正作十八点。依次排列,则这场夜宴席次如下(案图中虚线表示炕沿。又秋纹、碧痕、小燕、四儿四人的席位系随意安插,只是四儿和小燕的位置是考虑到了她俩儿年龄最为幼小):
俞平伯的《怡红院群芳夜宴图》
两相对比,一是谁在炕上、谁在地下,这个大的区别没有改变;二是炕上人的席位次序也没有变化;三是地下人中麝月和秋纹的位置做了对调,关键是麝月由晴雯的左侧改到了右侧——这是由于冯钟云先生把湘云掷出的九点改订为八点,而俞平伯先生乃是改作十点,麝月的点数则是随着湘云点数的变化而做的调整。另外,还有一个显着的变化,这就是把冯氏的两张方桌相拼,改成了并列的两张椭圆形炕桌。这一点虽很重要,但在此可以姑且不谈,留待下文再说。
俞平伯先生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题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撰写于1948年5月。此文发表在当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丛刊》上,后来收入俞氏在1950年编印的《红楼梦研究》一书中(案俞氏绘制这幅图的时间大大早于文章的撰写时间,初稿完成于1936年8月,重订定稿的时间是1947年9月)。
俞平伯先生的工作做得很认真,可周绍良先生却很不满意俞氏复原的这幅《怡红院群芳夜宴图》(案俞氏乃自颜其图曰“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席次图”)。原因,是按照俞氏的复原方案,对《红楼梦》原文中的色子点数,“有两处必须改动”。这样的做法,类似所谓“改字解经”,严谨的学者是一定要慎重其事的。
于是,周绍良先生重新解读《红楼梦》的叙事,绘制出这样一幅示意图:
周绍良的《怡红院群芳夜宴图》
图中用“XX”表示的四位与宴之人,是秋纹、小燕、碧痕和四儿,因为无法确定其席位,姑且如此处置。
周绍良先生这项研究,题为《〈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名称同俞平伯先生的文章很相近(收入周氏文集《红楼梦研究论集》)。与冯、俞两位先生的复原图相比,眼前这幅周氏《夜宴图》最突出的特点,是席位上多增入翠墨一人,使这场宴席的总人数由十六人增至十七人。不过这种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区别并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最大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乃是确定诸人席次的色子点数算法。
前面已经谈到,人们在喝酒行令时数算色子点数的方法,同打麻将等各种棋牌类博奕数算色子点数的方法一样,都是从掷色子者本人开始向右手的下家顺序数算,即第一就是掷色子的人。然而周绍良先生不知是不是从小家教太严,好像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类活动,竟以为色子点数的数算方法应该是“除了本人而望前数”。
我生长在东北那个没有入流文化的蛮荒之地,很小就打麻将、推牌九,做过很多下里巴人的勾当,因而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样的算法当然是大错而特错的。然而如此怪异的算法,所得出的结果,并没有显得特别荒唐,反而看起来好像还更合理一些。原因是新增入的翠墨被安置到了一个“适宜”的位置,对排列宴席的席次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既然如此,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翠墨究竟是不是参与了这场夜宴。
前面已经谈到,这场晚宴本来只有宝玉和他名下的八个丫鬟参加,可以说仅限于怡红院的主子和他的婢女。为了热闹,宝玉想到要占花名行酒令,如晴雯所云:“正是早已想弄这个玩意儿。”不过袭人说道:“这个玩意虽好,人少了没趣。”于是小燕首先提议请来宝姑娘和林姑娘。袭人担心请她们时在园子里“开门喝户的闹”,被大观园中巡夜的纠察,宝玉就说干脆一并请来当时主持荣国府内事的探春(宝钗虽然也受探春之请,协助料理大观园里的事务,但她只是在贾府做客,处事又极谨慎,所以只是勉强答应而已,不会实际干预相关管理事宜),还有同日过生日的宝琴。机敏干练的探春虽然很高兴,但考虑到当时在名义上她只是辅助李纨执事,而且宝琴还临时寄居在李纨那里(见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不请李纨,倘或被他知道了不好”,于是:
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二人,会齐,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
随后,“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当晚“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全体人员就是这么凑成的。不过曹雪芹这段行文有一处严重疏忽,这就是没有交待史湘云是怎么“冒出来”入席的(案冯钟云、周绍良两位先生论及怡红院中请来的客人,都没有注意到宝玉打发丫鬟去请客人时并没有提到湘云,实际上史湘云应与宝钗同请同来,因据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和第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当时她是住在宝钗那里)。
当时是小燕和四儿分头去请客人,小燕负责请探春和宝琴,四儿负责请宝钗和黛玉。请大家注意,这里所说“会齐”,是指李纨和宝琴二人随同翠墨、小燕这两位丫鬟“会齐”到了探春的住处,然后她们三人再一同前往宝玉住的怡红院。
翠墨是探春的丫鬟,请李纨是探春的主张而不是宝玉最初的安排,所以探春才会命翠墨和宝玉的丫鬟小燕一同去请李纨和宝琴;也就是说,翠墨实际是受自己主子的差遣把李纨先请到探春居住的秋爽斋(由于小燕还要一并请上宝琴,所以她才陪同小燕也去请了宝琴)。这样,既然已经完成了主子交付的使命,把李纨请到了秋爽斋,翠墨也就没必要再跟到宝玉住的怡红院去了。从书中上述描写来看,也不应该得出那样的认识。因为连李纨也没有带自己的丫鬟赴宴,引导她到怡红院的,是宝玉打发来的小燕。过去邓云乡先生曾写过一篇《“怡红夜宴图”辩》,就是这样判断俞、周二人的正误得失(邓文见所著《红楼识小录》)。
周绍良先生的席次复原工作既然存在根本性错误,其他细节也就没有必要多加讨论了。邓云乡先生在辨析俞平伯和周绍良两位先生的观点时曾经谈道:“我很愚顽,创造不出第三种‘图’和‘说’。”这当然是他以“愚顽”这一谦词讲出的自己认识,不过这样的认识却未必得当,也就是说邓氏肯定的俞平伯说未必真的像他以为的那样合理可从。
问题主要出在书中所记诸人掷出的色子的点数上。在这方面,邓云乡先生实际是有所涉及的,他说:“俞图的说明,虽有存疑处,但因各种版本不同,抄写、翻版者于此等处,均以为作者系虚拟,并未加认真推算,因之数字上刻错,未加注意校阅,各本出现差异,这是可以理解的。”诸本在色子的点数上出现差异,这固然可以理解,“无错不成书”嘛。不过这些色子的点数是确定怡红夜宴席次的主要依据,依据错误的点数,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复原呢?这是在复原《怡红院群芳夜宴图》时非较真儿不可的事儿。
我们看冯钟云先生对点数的订正方式,就与俞平伯先生明显不同,从而导致俩人复原的席次也有显着差别。又前面已经谈到,周绍良先生不满俞平伯先生的复原,是因为俞氏的复原方案必须改动两处色子的点数,并且说按照他提出的“十七人排列座次”,色子的点数“是完全无误的”。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周绍良先生是像俞平伯先生一样把麝月掷出的点数由十点改为十八点之后才做出他的复原图来的。
这种情况就告诉我们,准确复原怡红夜宴的关键因素,应该是从《红楼梦》的版本入手,审定当时掷出的色子点数。
在这方面,多少有些费解的是,俞平伯先生是大名鼎鼎的“新红学”开路先锋,周绍良先生虽然不愿意认领红学专家的身份,但不仅对《红楼梦》深有研究,对该书版本尤为用心收藏,可是他们却都没有想到需要花功夫去核对一下其他重要的版本(周绍良先生的文章最初发表在1980年9月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四辑上,而庚辰本早在1955年就已经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
当然,现在研究的条件比这些前辈们已经要好很多,简单核对一下人民出版社以庚辰本作为底本印行的冯其庸校勘本(2022年版),就可以看出,当时席上诸人掷出的色子点数应当是:
晴雯——五点(程乙本讹作六点)——宝钗
宝钗——十六点——探春
探春——十九点——李纨(令云“下家掷骰”)
黛玉——十八点——湘云
湘云——九点——麝月
麝月——十九点(程乙本讹作十点)——香菱
香菱——六点——黛玉
黛玉——二十点——袭人
依照这样的点数(案由晴雯起令,是由于这场夜宴真正的东家实际上是袭人、晴雯等八个丫鬟,钱都是她们出的,所以宝玉第二天才会对袭人讲“昨儿有扰,今儿晚上我还席”),试做怡红院群芳夜宴席次图如下(图中黄色粗线表示炕沿,绿色线条表示窗户):
我的《怡红院群芳夜宴图》
色子点数虽然是做出上述复原的主要依据,但做出这样的复原图还需要参考其他一些因素(色子点数根本没有涉及宝琴,但数算下来在那个位置上剩余一个空位,非她莫属),兹陈述于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冯其庸校勘本在这些色子点数上,除了探春的十九点是依据甲辰本勘正的数字外(勘正的结果同于程乙本),其余诸人掷出的色子点数,都一如其底本庚辰本原貌,可俞平伯先生后来在读到庚辰本和戚序本之后,不仅没有依据庚辰本来订正自己过去的认识,反而说道:“麝月掷个十点,原依程本。顷检脂庚本及戚本俱作麝月掷个十九点,仍与我的悬猜微差,但十九、十八,点数已很接近了。校记‘十’下疑脱一‘八’字,得脂戚两本证明,果然有脱文,亦一快也。”“十九”和“十八”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点数,俞平伯先生这“快”点真是太低,也太怪了。庚辰本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俞平伯先生过去依据程乙本做出的推论完全是错误的!岂有他哉!
下面再具体说明我在绘制这幅复《怡红院群芳夜宴图》时除了色子点数,还考虑了哪些相关的因素。
首先是炕桌的样式。前面讲到的三位前辈学者,冯钟云先生明确说是“方桌”,俞平伯先生画的是两个椭圆形炕桌,周绍良先生的复原最为怪异——按照他的画法,应该是一张方桌斜着放,一半在炕上,另一半悬在炕外的地面之上。
这场夜宴,由于最初只是宝玉和自己的八个丫鬟聚餐,所以在形式上搞得相当随便。袭人说:“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绰,又便宜。”桌上的食品也很随便,虽然“山南海北,中原外国,或干或鲜,或水或陆,天下所有的酒馔果菜”应有尽有,但毕竟只是装在四十个小茶碟里摆上来的小吃。这种圆炕桌,应当大致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圆炕桌
俞平伯把炕桌画成椭圆形,同书中描写的情况不符,也不便合理地排列诸人的席次。
本来这样一张圆炕桌,是够宝玉和他的八个丫鬟坐的。当时的情况是:因为随便,宝玉就命大家都卸装宽衣再上坐;桌子是靠着炕沿放的,所以“小燕、四儿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两张椅子,近炕放下”。
这主婢九人正要举杯欢宴,为更热闹些想占花名行酒令,这就需要有更多的人入席才能玩得嗨。所以如前所述,请来了李纨、宝钗、黛玉等七个人。这么一大帮人,一张圆炕桌就怎么也坐不下了。于是在“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方坐开了”。因为原来炕上的桌子是圆桌,所以,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这张新并上来的也应该是一张圆炕桌(我的《怡红院群芳夜宴图》之所以让桌面伸出到炕沿外边一块儿,是因为若不这样,炕沿下的那八个丫鬟大多数人就更够不着桌子了)。
并在一起的两张圆炕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席次是怎样安排的。李纨等七人加入之前,本来不必太讲究规矩,可李纨是大嫂,其他姐妹也都是请来的客人,这就不能乱来了。所以桌子可以接着往炕上并,座位却得照规矩安排。具体的座位序次如下。
第一,主子坐炕上,婢女搬椅子坐地下。
第二,炕上的主子,是以右为尊,在把相并的两张桌子当作一张桌子看的前提下,依照年齿排定的座次。
由于总数是八个人,第一位李纨,是坐在中央偏右的位置上;第二位宝钗,便坐在了她的左手。第三位黛玉,依次坐在了李纨右手;接下来的探春、湘云、宝琴,都是按岁数大小依次安排(案俞平伯先生不知为什么,说“宝钗首坐,李纨二,探春三,黛玉四”。同样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他要让宝钗和李纨独坐一面,把她俩突出出来)。
宝玉的年龄比黛玉、探春等都大,但他是主人(尽管这场夜宴实际做东的是他的八个丫鬟,可相对于请来的宾客,当然得由他来充当主人的角色),所以坐在主子的末座。
香菱的身份是薛蟠的小妾,只是半个主子(香菱是有自己的丫鬟的,名臻儿,见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所以虽然上了炕,却只能坐在最末的一个位置。席间袭人掣出“桃红又是一年春”的花名签时,因酒令要求“杏花陪一盏,坐中同庚者陪一盏,同辰者陪一盏,同姓者陪一盏”,“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庚,黛玉与他同辰”,就是刻意借此点明香菱与袭人不同于其他那些主子的身份,虽同庚而不能同等对待。袭人是婢女,还只能坐在炕沿下边,这很容易看出,而香菱的席位就很有必要做出这样的说明了。
第三,地下婢女的座次,是按照她们的地位和年龄排次,同样是以炕上主宾李纨为中心来定右尊左卑的序次。首先袭人等八个丫鬟,是分为大丫鬟和小丫鬟两个等级的:袭人、晴雯、麝月和秋纹是大丫鬟,芳官、碧痕、小燕、四儿是小丫鬟。袭人向宝玉讲她们筹办这次寿筵的费用时说:“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芳官、碧痕、小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这就是按照大丫鬟和小丫鬟地位高低分担的份额。
大丫鬟中袭人年龄最大,地位也最高(大丫鬟亦分为两等,头等丫鬟的“月例”为一两银子,二等丫鬟的“月例”为一吊钱,因为此前王夫人已经用自己的私房把袭人的“月例”提高到二两银子外带一吊钱的姨娘级别,也就成为事实上的小妾而同香菱平级了。事见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所以在八位婢女中位居第一,紧挨在宝玉的身边。
晴雯虽与袭人同岁,但生日稍晚,同时她是大丫鬟里的二等丫鬟,“月例”钱只有一吊(见第三十六回),地位比袭人低很多,所以便居于袭人的下位。
婢女中的芳官的座位有些特殊。按道理她身为小丫头,是没有资格排在麝月、秋纹之前的。然而宝玉特别宠爱她,才特地安排她参加晚上的宴席,而且她在宴席上还要给大家唱曲儿,所以破格排在晴雯之后的第三位。
接下来的麝月和秋纹两位大丫鬟,从资历上看,当然麝月应比秋纹大,也比秋纹地位高,所以一定是先麝月,后秋纹。另外,曹雪芹在书中写出的色子的点数,婢女中没有涉及到的只有四人,其中三位是小丫鬟碧痕、小燕和四儿,大丫鬟只有秋纹一人,这也显示出秋纹的辈分和地位在大丫鬟中是比较低的。
过去冯钟云、俞平伯和周绍良这几位先生,对秋纹、碧痕、小燕和四儿的座位都无从着手,而先确定这场夜宴席次的排列规则之后,就能合理地推断出这四个丫鬟的座位。
秋纹的座位推定之后,剩下的碧痕、小燕、四儿这三个人座位,还可以进一步推定碧痕应排在秋纹之下。
这是因为在李纨等与宴之前,只有宝玉和他的八个丫鬟围坐在一张圆炕桌边的时候,小燕和四儿就是坐在炕沿边的椅子上;宴席开始前被打发出去请探春等客人的丫鬟也是小燕和四儿(小燕去请探春和宝琴,四儿去请宝钗和黛玉),这都显示出她们俩即使是在这几个小丫鬟中地位也是最低的。不过在她们两人之间,年龄谁大谁小,就无从考证了。
我在复原图上把小燕排在四儿的前面,是因为书中提到她俩儿的时候总是先小燕,后四儿。小燕和四儿的座位确定之后,剩下的碧痕就别无选择,只有麝月身边那一个空位了。
按照这样复原的夜宴席次,可以较好地解释书中一些相关的描述。
首先是黛玉的坐法。书中记述黛玉入席的情景说:
宝玉忙说:“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垫着些。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黛玉却离桌远远的靠着靠背。
按照这样的描写,黛玉实际并没有坐在我在图中标记的席位上,而是远离桌面靠在宝玉身后那一面墙上,这才是“这边靠板壁”的地方,这样也才会“离桌远远的靠着靠背”。
正因为黛玉是这样一种特别的坐法,所以湘云才会在席间拿着探春的手“强掷了个十九点出来”——黛玉靠在板壁边儿上不挡她,李纨和宝钗又不坐在桌子最靠里头的顶点上,是稍微偏在两张桌子相接那一面。这虽然也有些费劲,但勉强还能够得着,可黛玉若是紧靠桌子坐在本来的位置上,湘云就怎么努力也无法拿得着探春的手。
附带说明一下,按照俞平伯先生复原的这场夜宴图,两张椭圆形的桌子分开很远,实际上是自成一席,同这些人共行酒令的情况不甚契合;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史湘云怎么越过黛玉、李纨和宝钗而去拿住探春的手掷色子,就实在无法想象了。
还有湘云掣签后书中述云:
掣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饮一杯。……恰好黛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饮。宝玉先饮了半杯,瞅人不见,递与芳官,端起来便一扬脖。黛玉只管和人说话,将酒全折在漱盂内了。
黛玉“将酒全折在漱盂内”,当然不宜让别人看见,这也只有远离桌边而漱盂又在手边才不易被人发现。另一方面,宝玉能够在自饮半杯后把酒偷偷递到芳官手里,则是因为炕沿下的丫鬟们挤不开,袭人的座位在序次上虽然属于丫鬟们最尊的位置,可是却无法靠近桌边,这就使得芳官看似与宝玉之间隔着袭人,实际上两人在桌子边上是相邻的,这样就很便于宝玉传递酒杯。
宝玉让芳官代自己饮酒,实际上是想让她多喝一些,过足酒瘾。前面谈到,她是因为受到宝玉的深情宠爱而特地让她参与这场酒宴的。当时,芳官就向宝玉说道:
若是晚上吃酒,不许教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学了这劳什子,他们说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没闻见。乘今儿我是要开斋了。……晚上要吃酒,给我两碗酒吃就是了。”
宝玉当即应允“这个容易”(第六十二回)。所以宝玉打破常规,把芳官的座位安排得靠近自己,也有便于给芳官劝酒和像这样让芳官替自己喝酒的考虑。
最后再谈一下这场夜宴席次的方位。这个问题,冯钟云和周绍良先生都没谈,只有俞平伯先生考虑了方位问题。
俞平伯先生拟定方位的依据是:(1)作为这场夜宴实际上的主人,宝玉“不会一上来就高高地坐在上首罢,当是下首”,所以,宝玉和黛玉“应靠西板壁而坐”;更准确地说,宝玉乃坐在“西首炕边,在炕上的末位”。(2)“依据点数及其他叙述,知居黛玉左侧者尚有五人。若黛靠东壁,即左壁,这五个就没处坐,得坐在炕沿下去,而炕上反空空如也,显然于情事不合”。——这两点依据,都相当怪异,而且几乎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第一,单纯就东西方位而言,主人居东面西,坐西朝东为客人的尊位,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要不怎么会有东家、东道、做东和西宾、西席这些说法呢?那天下半晌探春说是给平儿过生日的宴席,实际上是一并庆贺宝玉、宝琴、岫烟和平儿这四位同日出生者的生辰,当时的席次是“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儿面西坐,宝玉面东坐。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相陪”(第六十二回)。
这里明确讲到“宝琴、岫烟在上”,也就是说她们两人位居上位。探春做出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因为她们二人都是贾府的客人。由于宝玉和平儿是东西相对,所以宝琴、岫烟的座位也就相当于夜宴上李纨、宝钗的位置,从而可以确定怡红院的这场夜宴,是以李纨、宝钗一方为尊位的。
宝玉居西面东,位置显然尊于平儿。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宝玉不是这场宴席的主人(这场宴席也不是在他的怡红院里举办的,而是设在芍药栏中的红香圃这个大观园里的公共空间),而平儿只是贾琏的通房丫鬟。丫鬟就是丫鬟,即使成了通房丫鬟也还是丫鬟,属于女婢,地位比香菱还要低。能够上席同主子贾宝玉一起过生日,已经是很破格的礼遇了,无论如何平儿也不能坐到宝玉的上位去。没看她陪凤姐吃饭,是“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么(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探春特地“接了鸳鸯来”相陪,就是考虑到平儿身份的特殊性——鸳鸯虽然只是个丫鬟,却是贾母身边像管家一样的头牌婢女,正同平儿在凤姐那里的地位相当。
前面谈到宝玉的席位是炕上主子的末位,因为在他席位之后的香菱只是半个主子,但宝玉在这个位置坐,还有一个东西方位的原因——就是这里靠东面一头,他是做东的主人,就宾主关系而言,他也只能坐在东侧。
第二,俞平伯先生所说因“黛玉左侧者尚有五人”她就只能坐在西壁之下,这说法实在毫无道理,大家看一看我的《怡红院群芳夜宴图》,黛玉左侧的那五个人不还是好好地坐在炕上么?怎么非“得坐在炕沿下去”不可?
北方坐北朝南的屋子,炕都是东西向延伸,而人躺在炕上睡觉是呈南北向的,所以炕的宽度都是比普通人身高稍稍多出一点儿。不过这种炕有南炕、北炕之别。南炕向阳,显然优于北炕。所以,一般来说,人们是以南炕为优位的。
还有宝玉和黛玉背靠着的“板壁”东墙,显然只是分割房间的间壁墙,而不是作为外壁的山墙。因为北方天太冷,板壁不能做外壁。宝玉因林妹妹怕冷而让她靠近东面这一侧,一者炕脚中央会有窗户,有凉风,所以黛玉不宜太靠近桌子;二者西侧背后是山墙,晚上也会直接透过来凉气,靠近西侧也不大好。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这场夜宴是在南炕上举行的,所以李纨、宝钗是坐在南面,背后靠着南窗。这样一来,西面那道硬山墙就不会开门,这个房间的门只能开在东侧宝玉这一边。又东、南、西三方既已确定,剩下的北方在哪一面也就不用再加考索了。
虽然不会有多少读《红楼梦》的人就会有多少种《怡红院群芳夜宴图》,但前述各位专家的看法不仅彼此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在我看来这些看法同《红楼梦》的描写差距更大,所以才壮着胆子也做了这么一幅我的《怡红院群芳夜宴图》。
2023年6月24日午间草记
2023年7月6日下午改定
上一篇: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和矿山救援两项技术竞赛将举行
下一篇:最后一页
-
辛德勇读《红楼梦》|我的“怡红院群芳夜宴图”
2023-07-11 -
PVDF行业下游市场需求旺盛 大单资金布局相关概念股
2023-07-11 -
高温天,多地开放驿站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
2023-07-11 -
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和矿山救援两项技术竞赛将举行
2023-07-11 -
中联重科高机板块上市再进一步 拟作价94亿置入路畅科技
2023-07-11 -
做伙伴和客户身边的数字化伙伴,华为已经准备好了!
2023-07-11 -
三大指数集体高开 房地产等板块走高
2023-07-11 -
“瘦山”结出“富果”
2023-07-11 -
全球医疗器械20强11家布局苏州
2023-07-11 -
移远通信:7月10日融券净卖出2.39万股,连续3日累计净卖出4.64万股
2023-07-11
-
天津这些地方又“见缝插绿”了!
2023-07-11 -
止跌回升,6月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1
2023-07-11 -
孝心服务40载 电靓澴川30年
2023-07-11 -
60余名“洋学生”组团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
2023-07-11 -
世界气象组织:南极海冰面积创6月历史新低
2023-07-11 -
暴风影音2011(暴风影音2)
2023-07-11 -
搜狐汽车全球快讯 | 丰田首次正式确认拟在泰国生产电动汽车
2023-07-11 -
极端高温“烤”验全球经济
2023-07-11 -
英国首相会见美国总统,重点讨论俄乌冲突等议题
2023-07-11 -
三地联手打造 京津冀地区首批入围 京津冀生命健康集群入选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队”
2023-07-11